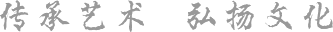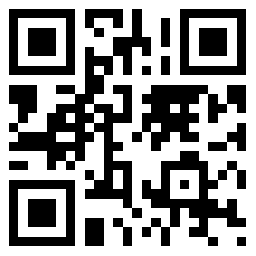贾植芳(1916—2008),山西襄汾人。现代作家、翻译家、学者。1936年留学日本大学社会学科。因投稿结识胡风,成为“七月派”骨干作家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历任震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复旦大学教授、图书馆馆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一届副会长,上海比较文学研究会第一届会长。专于中国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是这两个学科的奠基人之一。著有小说集《人生赋》,散文集《热力》《暮年杂笔》,回忆录《狱里狱外》,译有《契诃夫手记》等。有《贾植芳全集》十卷存世。
【生活再动荡也要握紧手中的笔】
◆哪怕生活再动荡,贾植芳也“总是在人生道路上任何一个安定的瞬间匆匆忙忙抓起笔来,努力要留下一些人生的感触”。甚至在化名避居青岛安身小客栈的时候,因为“穷居无事”,便“潜心翻译”。他从街头旧货摊上以买废纸的价钱购进一批英日文外文书,用不到半年的时间翻译了三本书:恩格斯的《住宅问题》、英国传记作家奥勃伦的《晨曦的儿子——尼采传》以及匈牙利作家E·维吉达的多幕剧《幻灭》。
【教授是假(贾)的,教书是真的】
◆贾植芳不是正襟危坐的老先生。他身上有着烟火气,幽默感无处不在,说话常常妙语连珠,调侃起自己来更是毫不客气。年纪大了,他说自己“走路用拐杖,谈话要用助听器,成了三条腿、三只耳朵的人,有时想想,觉得自己像个《封神榜》里的角色”。说到自己的工作,他说“我这个教授是假的,不是人人都叫我‘假(贾)教授’吗?不过,我教书却是真的,从来不卖假货”。虽是玩笑,但从中能看出老先生的人生智慧和职业坚守。
【学术眼光充满前瞻性和先锋性】
◆贾植芳的学术眼光非常前卫。他很早就具有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思维——上世纪50年代的课堂上,已经在用这样的思维方式授课;1980年代初,比较文学尚在复苏之中,贾植芳已自觉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对中国现代文学展开研究。在翻译上也是如此。他1940年代就翻译了恩格斯的《住宅问题》。解放初期曾有人做过统计,复旦大学有两位教授是译介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一位是陈望道,另一位就是贾植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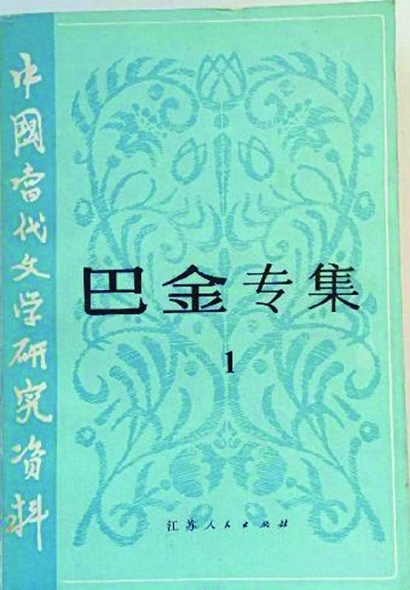
贾植芳代表作一览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巴金专集》
大写一个端正的“人”字
贾植芳为后人记住的,除了丰厚的学术遗产,还有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铿锵风骨。
在回忆文章《且说我自己》中,贾植芳说道:“在上帝给我铺设的坑坑洼洼的生活道路上,我总算活得还像一个人。生命的历程,对我来说,也就是我努力塑造自己的生活性格和做人品格的过程。我生平最大的收获,就是把‘人’这个字写得还比较端正。”这样的话,贾植芳说过多次。在他心中,不论是要做“人生的主人”,或是追求生命的不平凡,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写好这个“人”字。
“我只是个浪迹江湖,努力实现自我人生价值和尽到自己的社会责任,在‘五·四’精神的培育下走上人生道路的知识分子”,贾植芳晚年时的这番自我评价全面而深刻。他乘风破浪的一生,他的学术源起,“社会人”与学者的双重身份都在这一句话中交代得清清楚楚。
在许多人的心中,贾植芳的存在如精神标杆,他那由风浪也扑不灭的风趣、磨不掉的傲骨,常为人谈起。但内里对学问、对学科建设、对传道授业,他是极度认真的,从读书上学,走上“知识分子”之路开始,贾植芳就时时提醒自己知识分子的责任。后半辈子,贾植芳以全副身心投入到他所热爱的文学和教书育人的事业当中,在复旦大学中文系首创了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两门学科,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在学界赫赫有名的学者。
从 “淘气王”到半生动荡的“社会人”
如果在贾植芳孩提时代,问他的父母,这个小孩儿将来会长成什么样子,“学者”大概是一个最意想不到的答案。1916年,贾植芳生在山西吕梁山区一户家境殷实的地主家。因为总是闯祸,家里图清静,将5岁的贾植芳送入私塾,后来转到邻村小学就读。天性不喜约束的贾植芳对教材上的刻板内容毫无兴趣,父亲赶集买来的新课本别在他腰上,买一次丢一次,还时常在课堂上淘气。开始对书籍着迷,是贾植芳读高小的时候,那时同学借他一本石印本《封神榜》,贾植芳一下子就被情节吸引住了。上初中时,贾植芳走出了闭塞的山村到省城读书,那段时间他沉迷于各种借来的石印本小说,钦佩行侠重义的绿林好汉,佩服降妖镇怪的神道。转折发生于初二,学校来了一位北师大毕业的国文教师,指导学生们看新文学作品《呐喊》《彷徨》以及外国翻译文学和一些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政治读物,这对贾植芳影响尤深,“从这时起,我开始认识到文学是一种改造社会、改善人生的武器”。此后,贾植芳开始尝试写作、投稿,将对社会的观察和剖析付诸笔端。1931年,贾植芳到北平一所由美国教会主办的中学读高中,虽然读了两年半就因个性反叛被校方除名,但这段时间,贾植芳打下了坚实的英语基础。他开始看原版英语报纸和书刊,视野也随之放宽,更多的中外文学作品、社会科学译著列入他的阅读范围——在他宿舍的墙上曾挂过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克鲁泡特金、马克思的相片。
回望青少年时期,贾植芳曾自述:“我生逢中国社会内乱外祸交织、动乱不安的时代,这个时代也是一个中外文化交流、碰撞、融汇的开放性时代。在这样的历史环境里,我们一方面继承了儒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文化传统;另一方面追求着个人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投入了中国救亡和改造的社会政治运动。”1935年,血气方刚的贾植芳参加了“一二·九”运动,被逮捕关押,经当商人的伯父四处周旋才出狱。之后伯父匆匆将他送往日本求学,并叮嘱他不要再碰政治。到了日本后,贾植芳并没有遵从家里的意思学医或读银行管理,而是在1936年夏天进入了日本大学社会学系,跟随园谷弘教授学习研究中国社会,初衷是“想学点社会学专业知识,以便从中得到观察、分析、描写和反映社会生活的理论导引”。然而贾植芳最热衷的依然是文学,尤其是外国文学,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安特列夫代表的俄国文学尤其喜爱,甚至从旧书肆中搜购了他们作品的英译本和研究俄国文学的论著来阅读。贾植芳说,这些阅读,对他有过很深的影响。
1936年10月,鲁迅去世了。鲁迅是贾植芳唯一始终崇拜的中国现代作家,他从不隐藏这份喜爱和崇拜,多次在公开场合尊鲁迅为“精神导师”。暮年之际,饱经忧患的贾植芳每每重温鲁迅的早期作品,还能从中找到深切的现实感受。鲁迅的去世,给年轻的贾植芳带来不小的打击。不久后他在东京内山书店发现坚持鲁迅传统的战斗文学刊物《工作与学习丛刊》,非常惊喜,于是将自己的一篇小说寄送投稿。从此贾植芳与刊物主编胡风,也是鲁迅亲炙的弟子交上了朋友,后来成为胡风主编的《七月》《希望》等文学期刊的作者之一。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贾植芳当即弃学绕道香港回国参加抗战,期间拒绝了家人替他安排的留在香港或去欧洲读书的前程。后来谈起这次人生十字路口上的抉择,贾植芳说:“再想到自己几经囹圄、伤痕累累的一生,我不能不感慨万千……但选择回国抗战,仍然是我的良知所决定的”,“我仍然会选择自己应该走的路,终生不悔”。战争给青年贾植芳的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社会人”烙印:他在前线做过日文翻译,也为后方报纸写过战地通讯……他不服管束的个性和刻在骨子里的良知使他不能容忍现实中腐朽与黑暗的一面,以至于几次险象环生,几次绝境逢生,整个抗战期间在大半个中国颠沛流离。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贾植芳因在徐州搞策反被关到了日军的牢房;1947年9月到上海后不久,因给进步学生刊物写文章,又受了一年多的牢狱之灾。多年在流转生活中打滚,贾植芳养成了一种习惯和嗜好:读各类有关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书,以便能深入认识和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和现实。1948年再一次从监狱中出来,贾植芳便蛰居沪西乡间一阁楼,用两个月时间,趴在两只箱子搭成的临时书桌上,依靠借来的图书资料——多半是日本学者的著译,和他常年对社会的观察,昼夜不停地编写了一部20多万字的社会学著作《近代中国经济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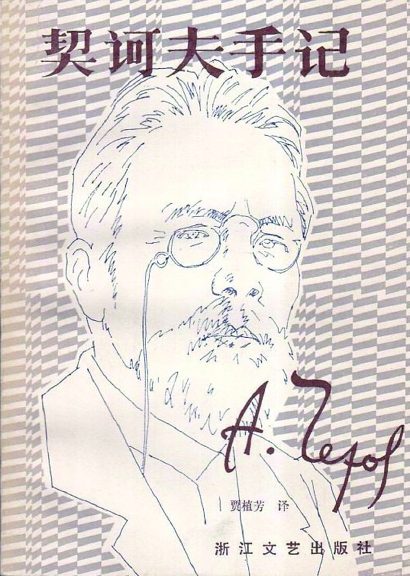
贾植芳译著《契诃夫手记》
中国现代文学是与他的生命血肉相关的历史
“贾先生是‘五四’的第二代。与前面一代的知识分子相比,他们是在‘五四’反封建专制主义精神激励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却在青壮年之际遭遇了抗战,失去了窗明几净的书斋,失去了从事缜密研究的环境。因此贾先生的文学知识积累不是书本到书本,而是活生生的感受。”著名学者陈思和曾跟随贾植芳读书,在他眼中,现代文学是活的历史,某种意义上还在延续;而贾先生是这段历史中的人,现代文学与他的生命血肉相关。“他得到的知识、做人的方式、爱憎分明的性格,对传统封建内容的批判,都有着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影子。新文学传统的激进文学传统里,代表性人物胡风、巴金以不同的方式继承了鲁迅精神,这种精神传统又在贾先生身上得到延续。”所以,贾植芳的现代文学课,更像是当事人对人生观察的分享,他讲述文坛掌故与作家背景,关于现代历史与文学的广博见识和真知灼见,时常就贯穿在闲谈中。作为贾植芳的学生,学者张新颖曾回忆,在他读研究生期间,贾先生没有给他讲过一次课。“先生的方式就是坐在书房兼客厅里聊天。聊什么呢?没有限定。这位瘦小的老人,能够让你充分感受海阔天空和人世沧桑。你在这里学习历史和认识社会,全是通过具体可感的形式。”在贾植芳的又一位高足严锋看来,贾先生的记述与回顾有着一种特殊的文化现场的意义,“他的这种‘目击者’的证人式的研究法就是贾先生的独门暗器,也是历史和磨难赠予他的珍贵礼物”。贾植芳一些有趣的生活习惯都与他独特的治学方式有关,比如他会去报摊上买小书小报,喜欢那些带着原始的、粗糙的,甚至乱糟糟的社会生活气息的真实的社会经验,而不是被知识分子的趣味所整理、阐释、概括和升华后的那些东西。
这些特质,都引向了一个看似偶然的必然:1950年,贾植芳从“社会”进入“书斋”,到震旦大学中文系任职,开始了以学术为业的职业生涯;后随高校院系调整,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授,并受命主持新组建的现代文学教研室——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上,贾植芳是学科创建的元老之一。这一时期贾植芳对现代文学学科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学科架构、课程设置和人员调配这些“看不见”的基础工作上。“他的工作为复旦中文系现代文学学科日后的长足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今天看来,复旦大学的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和研究所以能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与贾植芳先生当年的开拓性贡献分不开的。”贾植芳的再传弟子张业松在一篇回忆文章里写道。贾植芳一路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拓荒路上潜心耕耘,没有料到的是,与胡风的友谊让他陷入了一场长达25年的牢狱、“改造”风波。直到1980年底,贾植芳才获得平反,重新回到教授位置,这时他已经60多岁。但他的精神锐气未曾磨灭,在64岁到92岁留下了大量文字,这也是他一生中著述最为丰富的时期。
重启学术之路的贾植芳接续了断档20多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工作。当时,学科重建面临的最为紧迫的任务,就是重新梳理和抢救基础史料,还历史本来的丰富面貌。1980年代初,贾植芳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启动了大规模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先后参与主持编纂《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等大型资料丛书,并亲自承担了其中的《巴金专集》《赵树理专集》《闻捷专集》《文学研究会资料》等书的编选工作。编纂这些大型丛书是一件为后学栽苗植树的工作,为了将其做好,贾植芳留下了体量可观的审读和指导意见,并为专集撰写编后记,字里行间透出的正是他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复兴和发展的建设性的思路。在贾植芳看来,研究性书籍的编辑工作应该严格从文献学的角度、或者从历史的观点出发,要突破文学研究中的一些积弊尤其是钳制研究的非学术要求——在1980年代初提出这样的想法,需要非常大的学术勇气。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奠基人之一
“1980年代初的时候,比较文学还刚刚在复苏之中,贾先生谈起来就好像已经思考多年了。”比较文学研究学者严绍璗曾在一次采访中赞叹贾植芳学术思想的前瞻性和先锋性。贾植芳写于1981年的长篇论文《中国新文学作家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以茅盾为例》已在自觉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对中国现代文学展开研究。“其实,应该说在1950年代初他给章培恒、范伯群、曾华鹏诸位先生上课时,就已经参透着当下比较文学学科倡扬的学术思想”,严绍璗说。曾有当年的学生回忆,贾先生讲课常追根溯源,以异国文学相印证。讲台上堆一叠书,很多都是西方的著作,他当场翻译给学生听,学生的眼界豁然打开——贾植芳一直以来就反对孤立静止、画地为牢地自我封闭式地研究文学,“那是走古人研究四书五经的老规范:寻章摘句,咬文嚼字,只能是像马克思所鄙夷的那种坐在书斋里连手指头被烫伤都害怕的三流学者,或者像我们古人所形容的‘腐儒’,或‘书虫’,那就不可能在原有的文化遗产基础上进行创造性劳动”。
多年的翻译经验自然也是将贾植芳引向比较文学研究的关键。贾植芳译著丰富,且主要集中在学术研究文章上:他1940年代翻译了恩格斯的《住宅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专著的早期译者。解放初期曾有人做过统计,复旦大学有两位教授是译介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一位是陈望道,另一位就是贾植芳。而对捷克作家基希的《论报告文学》的翻译,更是显示了贾植芳的前卫眼光——报告文学这一战斗文学样式1930年代才引入国内,贾植芳作翻译时,同类译作寥寥。而对《契诃夫手记》的翻译更是他译著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在贾植芳眼中,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鲁迅起的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家,无不从翻译文学中吸取到珍贵的养料……翻译文学理应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这里其实透露出了贾植芳倡导比较文学的思想动因——他对中国文学的开放性的期盼,如他在《开放与交流》这篇短文中所说:“比较文学的一个基本精神就是开放与交流:以开放的眼光去研究文学的交流……比较文学研究的尽管是已有的文学现象,但它必然会带来各国文学之间的交流。而且,这种交流是双向的,即不仅有引进,还有引出。”
上世纪80年代,在贾植芳的倡导和推动下,复旦大学中文系恢复了比较文学的教学和研究,成为全国最早开设比较文学课程、最早设立比较文学教研室、最早获得比较文学硕土学位授予权的高等学府。没有先例可循。在贾植芳的手上,复旦大学的比较文学研究学科一点点“从无到有”。从资料梳理到理论评说,从建立学会到培养人才,他的工作逐步奠定了学科的规模、发展方向与品质。他当时主持的国家重点社科项目《外来思潮流派理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影响》,在成书出版时改名为《中外文学关系史资料汇编》,是国内第一部较为全面和系统地整理中外文学关系史文献的大型资料书,在学界影响深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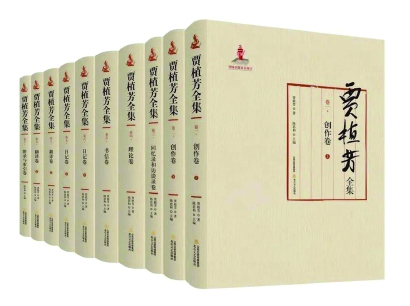
《贾植芳全集》
留下了学术遗产,也传承了人格精神
曾有人借贾植芳的日记观察过他的工作强度:“全力编《契诃夫年谱》,通宵达旦”(1983年3月30日),“昨晚译书至晨六时始寝”(1983年10月24日),“未出门,今日五时始寝,赶译论文”(1983年11月1日)……为什么要如此辛苦?老先生又露出了他嘻嘻哈哈的一面:“既然活在这个世界上,要活着就要消费,为了付饭钱,就得为这个社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玩笑的背后,其实是他一以贯之的知识分子的担当,还有来自青年时期的、从未熄止的理想之光。他有过另外一番剖白:“对我们这一代在‘五四’精神培育下走上人生道路的知识分子说来,凡是有助于社会进步和文化建设,即能促进中国由旧的传统走向现代化的大小活动,总是习惯性地卷起袖子,奔上去,自觉地做些什么,即或是为之出生存身,呐喊几声,擂鼓助阵,都当成是一种义不容辞的社会职责。”带着这一底色的贾植芳在青年时代形成了“当一个好事之徒的本性”,晚年更是甘做“写序专业户”,为把那些奋力于严肃的文艺著译与学术著作的后辈学者推向学术文化界而摇旗呐喊。直到生命的最后,睡在病床上,贾植芳伸手能够够到的地方全是书,一颗心仍在挂念着病房之外的事。
“他是魅力型人物”,陈思和说,“我明显感受到他那种强悍的、父性的人格对我的影响,这是一种整体的影响,包括后来我人生道路的选择,都与此有关。他教给我怎样做人,他并没有具体地教我该怎么做,但他待人处世,看历史,看现实,整体的精神深深影响了我”。深受贾植芳影响的不只陈思和。著名学者章培恒生前曾说过贾植芳对他的师恩是一辈子的,既在做人方面也在做学问方面。他坦陈自己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里面的“不正宗”正是袭自贾先生研究中国文学的方法和路径:“如果没有这样的一种指导,我当然还会做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但是跟现在的情况,可能会很不一样——而这一种很不一样在我来看并不是我所希望的,我应该说正是我所害怕的”。在陈思和看来,贾先生传授的是一种“知识分子的立场和精神”,即从正宗的主流的传统规范中走出来,通过个人的独立思考,重新审定研究对象。贾先生通过这种“精神传递”,“将优秀学生的才华充分调整到了一个火山口,接下来就让它自然地喷发了”。上世纪五十年代,短短几年贾植芳就培养了章培恒、施昌东、范伯群、曾华鹏等学生,他们后来分别成为古代文学、文艺美学、现代文学等领域的领军人物;而在八十年代重回教席后,贾植芳更是培养了陈思和、李辉、严锋、张新颖等学术领域内著名的学者。“优秀教师的判断标准是能否培养出优秀的学生,而不是自己是否有名。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贾先生是一名真正的教育家”,陈思和说。
“我理解的人生,不只是履行动物的本能要求……人生应该追求更高的生活境界——人生的自我价值和意义……应该通过博读精览,放眼人生、世界和历史,找到自己在生活中的真正位置,履行自己的人生责任和社会使命。”2002年,第五届上海市文化艺术特殊贡献颁奖典礼上,回顾过往,86岁的贾植芳说,我并未虚度一生。
来源:文汇报
-
 七绝·你我相投守信条
七绝·你我相投守信条
 10374
10374
-
 七绝·烟雨江南藏俊雄
七绝·烟雨江南藏俊雄
 10119
10119
-
 七绝·幸福日月自藏身
七绝·幸福日月自藏身
 10102
10102
-
 七绝·爱意慈悲有业因
七绝·爱意慈悲有业因
 10032
10032
-
 七绝·还有权谋生祸灾
七绝·还有权谋生祸灾
 9987
9987
-
 七绝·情感无声意味长
七绝·情感无声意味长
 9157
9157
-
 七律·仁义礼智信
七律·仁义礼智信
 8598
8598
-
 七绝·自驾游春三世间
七绝·自驾游春三世间
 8547
8547
-
 七绝·不屑红尘把爱抛
七绝·不屑红尘把爱抛
 8484
8484
-
 七绝·悄然梦醒是新吾
七绝·悄然梦醒是新吾
 8468
8468
-
 贺芳林《七律》望中国航母舰
贺芳林《七律》望中国航母舰
 2036225
2036225
-
 贺芳林《七律》风雨后相逢有
贺芳林《七律》风雨后相逢有
 1635161
1635161
-
 贺芳林《七律》春青重走长征
贺芳林《七律》春青重走长征
 1052993
1052993
-
 贺芳林《留春令》丝路追情
贺芳林《留春令》丝路追情
 774690
774690
-
 贺芳林《鹧鸪天》咏历雪梅花
贺芳林《鹧鸪天》咏历雪梅花
 558700
558700
-
 贺芳林《七律》金桂秋情
贺芳林《七律》金桂秋情
 503549
503549
-
 贺芳林《七律》秋晨登华山写
贺芳林《七律》秋晨登华山写
 471000
471000
-
 贺芳林《家山好》月来仙桂
贺芳林《家山好》月来仙桂
 350260
350260
-
 贺芳林《七律》登雪满长城感
贺芳林《七律》登雪满长城感
 346412
346412
-
 贺芳林《七律》秋吟晴霁岳麓
贺芳林《七律》秋吟晴霁岳麓
 331226
331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