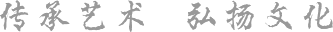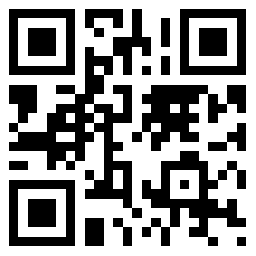秦立彦:“拿来”自己的传统
作者:秦立彦 来源:诗刊
上传时间:2019-05-28 10:04:46
浏览量:1835
收藏
手机看文章
扫码手机看文章
叶芝在《驶向拜占庭》一诗里说,要追随着大师们学习“歌唱”。写诗的人都有自己私心里拜过的老师。如果在今天的中国询问写新诗的人,你最爱的诗人是谁,你最服膺谁,你的案头上放着谁的诗?我冒昧地猜测,我们给出的答案会以西方二十世纪的诗人居多。我们自觉地把自己当成了西方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传人和火炬传递者。庞德在年轻的时候曾立下壮志,关于诗歌他要知道得比所有人都多。我们亦当如此,西方诗歌可以被我们“拿来”,而且已经被我们“拿来”,已经成为我们的一个重要资源。但另一方面,也许我们反而相对忽略了中国自己悠久的诗歌传统。如今五四运动已经发生了一百年,中国的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国际地位都在蒸蒸日上,我们可以说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历史时期。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重新思考中西诗歌传统的契机。
我常常想知道现代派诗人和理论家庞德,在遇见中国古诗的时候看到了什么。不懂中文的庞德经过几层转折,翻译了李白的《长干行》《送友人》,诗经中的《采薇》等。熟悉这些中国诗的我们再来看庞德的译文,会发现虽然形式上发生了许多变化,也颇有些硬伤,但从整体而言,那内容与风格就是《长干行》,就是《采薇》。这些诗朴素而单纯,与庞德自己创作的复杂、炫学的诗全然不同。他翻译的《长干行》是他的代表作,经常编入美国人最喜爱的诗选中。也许我们应该像庞德那样,以初次相遇的惊奇去看中国古诗。我们都熟悉《长干行》,但也许正因为太熟悉,使我们体会不到惊喜,就像以美女为妻的男子,久而久之就看不出妻子之美。庞德从中国古诗中看到了什么?是什么使《长干行》的女主人公那样打动西方读者?这是一种有趣的错位。西方现代派诗人从中国古诗中寻找灵感,从中国的诗歌传统中“拿来”,我们则服膺西方现代派。实际上我们看的外国诗歌主要是译文,读外文已经是隔一层,读译文就隔了两层。庞德吃力地透过好几层障碍去读中国古诗,但中国古诗的光辉透过这几层障碍,仍使他迷醉;而那些古诗是直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对我们而言是“不隔”的。这样看来,中国自己的传统是我们最容易继承的。这时我深深感到对这一传统我们若不去“拿来”,是对自己也是对这一传统的不公正。我们在远望的同时,也需要深知自己脚下的土地。
当代生活与唐宋简直是两个世界,但人们依然热爱那些诗词,它们依然说出了我们的心声。这就是诗的魔法。并非是当代的普通读者不怎么读诗了,他们一直在大量阅读李白、杜甫、苏轼。这些古代诗人得到的最大赞美,就是被他们无法想象的后世的人们所珍重和喜爱。
我们需要以另一种眼光,重新审视我们自己的传统。传统并不是天然地流淌在血脉中,它属于任何努力学习它的人。我们虽然是中国人,但不一定就承载着那些文化基因,它们是需要后天习得的。在五四之后和文革之后,中国的古诗传统于写新诗的人而言其实是有些外在的,我们对艾略特的熟悉或许超过了对杜甫的熟悉。而庞德告诉我们,在新的情境、新的眼光下,旧的可以变成新的,古物可以焕发青春,成为写作者们活的源泉。
我们感到庆幸的是,我们有无尽的新题材,许多现代生活的经验尚未表达为诗。在形式上我们有新的自由,此外再加上西方诗歌对我们的影响与熏陶。而当代写旧体诗的作者们面临的困境是很容易被那些古代大师们困住手脚,难以挣脱。对偶、平仄、用韵、用典——这些是今天写旧体诗的人们依然需要考虑的,如何用旧体诗表现当代经验则更是一个难以处理的问题。而写新诗的人则无需面对这些问题。
那么,我们从中国古代诗歌传统中继承什么呢?当代的人们喜爱读古诗,部分是因为古诗可以治疗现代病,缓解现代生活的原子化与孤独,给人们带来安慰。有很多古诗的题材都是送别、宴饮,有的诗人干脆以诗词为书信。古诗不是抽屉文学,承担着重要的人际功能,是人与人联系的手段,发挥着“兴观群怨”中“群”的作用。我们现在未必唱和、联句,也不一定要在宴会上各自赋诗,但中国古诗提供了诗的另一种可能性:诗是自我的,同时也是公共的,是服务于人的。诗中所描述的经验未必是完全私密的,诗的效果来自于言人所未言,此言未曾被他人道出。而说出众人的情感,说出众人想说而未说出的公共经验,追求共鸣,抵达尚未有语言抵达之处,这给我们带来了另一种想象诗的功能的路径。
中国古诗的美学也给我们以启发,那就是中国式的境界和气象。在纷繁的风格花园里,中国古诗提示了一种温柔敦厚的、内敛的风格。古诗从诚挚的本心出发,关注自然风物,关注草木,追求情感与风景的融合。同时,古诗强调意在言外,在诗中留白,不把意思点破、说尽。这些都可以为我们提供重要的启示。
我想中国古诗在技艺上对我们的启发是最大的,因为我们和古人用同一种质料工作,这个质料就是中文。在这一点上,外国诗歌不容易帮助到我们,尤其当我们阅读的是译文的时候。“艺术”一词的拉丁语是 ars,既是艺术,也是技术;“诗人”一词在希腊语中是 poeta,既指诗人,也指一切制作者。诗歌是一种技艺、一种能力。黄永玉说:要比较画家们的能力,可以请大家对着米兰大教堂写生,作为考试。自如地使用颜料,熟悉色彩的细微对照,光影的细微变化,然后才能成为画家。具有了这种能力之后才谈得上表达自己的想法,实现自己的意图,否则一切都是空中楼阁。诗也一样。无论多么好的诗思,最后还是要落实为一个一个的汉字。汉字就是我们的颜料,就是“轮扁斫轮”故事中的木料。叶嘉莹先生说她曾见过一些情感丰富、观察敏锐的人,但他们并不能诗,因为没有这方面的训练。古体诗的写作如此,新诗也如此,并非是谁都可以舌绽莲花、咳唾成珠的。诗歌的能力主要不靠天生,而靠后天习得,正如李白那样的天纵英才很少,而杜甫那样的勤奋劳动者才是我们的榜样。
中国古诗词的篇幅都不长,题材又常常相近。这给了我们一种错觉,以为它们是重复的,空间狭窄,内容有限。但它们告诉我们的正是如何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腾挪,如何戴着脚镣跳舞。大家都写望月,写怀远,但效果天差地别,于是苏东坡的中秋词一出,千古中秋词尽废。在“写什么”上,我们这些当代的写作者有更大的自由,而我们恰恰可以从古诗中学习“如何写”。
我们可以学习古诗词的篇章结构,如何起承转合,如何开始,如何结束,什么时候斩钉截铁地结束,什么时候有余不尽地结束,何处浓墨重彩,何处留白。在深入阅读古诗词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获得对中文的“手感”,辨别词语的温度、湿度,浓与淡、轻与重、动与静、哑与响。这种追求也正是福楼拜所说的寻找“唯一准确的词”,也就是炼字。为什么“春风又绿江南岸”优于“春风又到江南岸”?为什么“漠漠水田飞白鹭”优于“水田飞白鹭”?对此中国古人费了许多心力,做了大量的工作,因为他们的目的未必是文学理论的建构,而更在于分辨好诗,写好诗。远到古人的许多诗话、评论,近到叶嘉莹先生等做的细读古诗词的工作,都可以成为我们的资源。
中国是诗歌大国,我们是诗歌大国的子民,诗歌巨人们的后裔。在以西方诗人为师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自豪地以中国古人为师。我想,现在可能是我们重估中国古代诗歌对我们的价值,把自己的传统重新“拿来”的时候了。
作品热度榜
日
周
月
总
-
 贺芳林《七律》风雨后相逢有
贺芳林《七律》风雨后相逢有
 1572172
1572172
-
 贺芳林《七律》望中国航母舰
贺芳林《七律》望中国航母舰
 1160587
1160587
-
 贺芳林《七律》春青重走长征
贺芳林《七律》春青重走长征
 1025657
1025657
-
 贺芳林《留春令》丝路追情
贺芳林《留春令》丝路追情
 644380
644380
-
 贺芳林《七律》金桂秋情
贺芳林《七律》金桂秋情
 486678
486678
-
 贺芳林《鹧鸪天》咏历雪梅花
贺芳林《鹧鸪天》咏历雪梅花
 486459
486459
-
 贺芳林《七律》秋晨登华山写
贺芳林《七律》秋晨登华山写
 452941
452941
-
 贺芳林《家山好》月来仙桂
贺芳林《家山好》月来仙桂
 334517
334517
-
 贺芳林《七律》秋吟晴霁岳麓
贺芳林《七律》秋吟晴霁岳麓
 314975
314975
-
 贺芳林《七律》登雪满长城感
贺芳林《七律》登雪满长城感
 305967
305967
诗家热力榜
日
周
月
总